男女主角分别是陈砚明林晚秋的其他类型小说《岁月逢花无删减全文》,由网络作家“用户酒窝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天来的,挎着个蓝布包袱,一开口带着泥土味:“大妹子,能补补这裤子不?俺家虎娃爬树刮了个大口子。”打开包袱,是条补丁摞补丁的灯芯绒裤,破口处还沾着草汁。林晚秋摸了摸布料,硬邦邦的补丁底下全是线头,显然是用家里的旧被面凑合缝的。“补补丁一块钱,”她指着价目表,见张婶眼皮子一跳,赶紧补充,“我用的确良布给你补,比原来的结实,再绣个小虎头,虎娃肯定喜欢。”说着从帆布包里翻出块橘色碎布,边角料是她从百货公司裁缝铺捡的,“你看这颜色,耐脏。”张婶的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,突然从裤腰里掏出个塑料袋,层层剥开是两张一元纸币:“大妹子你给俺多绣两针,虎娃他爹在公社开拖拉机,下月发了粮票给你带新布料。”夜里收摊时,林晚秋数着铁盒里的硬币,五毛、一元、还有几...
《岁月逢花无删减全文》精彩片段
天来的,挎着个蓝布包袱,一开口带着泥土味:“大妹子,能补补这裤子不?
俺家虎娃爬树刮了个大口子。”
打开包袱,是条补丁摞补丁的灯芯绒裤,破口处还沾着草汁。
林晚秋摸了摸布料,硬邦邦的补丁底下全是线头,显然是用家里的旧被面凑合缝的。
“补补丁一块钱,”她指着价目表,见张婶眼皮子一跳,赶紧补充,“我用的确良布给你补,比原来的结实,再绣个小虎头,虎娃肯定喜欢。”
说着从帆布包里翻出块橘色碎布,边角料是她从百货公司裁缝铺捡的,“你看这颜色,耐脏。”
张婶的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,突然从裤腰里掏出个塑料袋,层层剥开是两张一元纸币:“大妹子你给俺多绣两针,虎娃他爹在公社开拖拉机,下月发了粮票给你带新布料。”
夜里收摊时,林晚秋数着铁盒里的硬币,五毛、一元、还有几枚二分的钢镚,总共三块二。
缝纫机的踏板上沾着几根彩色丝线,像落了片迷你的虹。
她想起刚才张婶摸着绣好的小虎头笑,说“比买新的还经穿”,想起女工穿上改窄的裤子在路灯下转圈,裤脚刚好露出脚踝——原来她的针脚,除了给男人补军装、给病人做病号服,还能让这些沾着机油和泥土的女人,在疲惫的生活里多出一道细巧的褶边。
铁皮顶棚被风吹得哐当作响,隔壁烤红薯的炉子飘来甜香。
林晚秋用旧报纸裹住缝纫机,突然摸到踏板底下自己垫的棉絮——那是从离婚时带走的棉被里拆的,边角还留着当年给陈砚明绣的平安纹。
她指尖顿了顿,又把价目表往摊位前挪了挪,粉笔字在路灯下白得发亮,像落在黑夜里的星星。
“大姐,这裤子怎么卖?”
穿喇叭裤的姑娘停在摊前。
“八块。”
林晚秋声音发颤。
姑娘翻看裤腰,突然笑了:“这针脚比百货大楼的还密,就是花色老气了点。”
她掏出钱:“给我改条喇叭裤吧,我带布来,加工费你说多少?”
夜市的灯忽明忽暗,林晚秋握着粉笔在木板上写下“来料加工,量体裁衣”。
收摊时,裤兜里多了三张皱巴巴的五元钞票,还有三张记着顾客尺码的纸条。
她摸着缝纫机冰凉的铁架,突然想起十七岁在县服装厂当学徒,师傅说
市场,夜里在仓库打地铺。
有次暴雨冲垮仓库,她们抢救出的布料堆在马路上,林晚秋踩着积水大喊:“这些料子能做三百件风衣!”
路过的货车司机停下车,帮她们把布料搬到安全地带。
后来这个司机成了她们的物流合作伙伴。
11 缝纫机上的星光1990年,林晚秋的服装公司在红T时尚创意街区挂牌。
开业典礼上,她特意请回当年的车间主任。
老人摸着数控裁床直摇头:“当年训你最狠,没想到你把厂子带出了泥沼。”
林晚秋笑了,眼角的细纹里藏着二十年的月光:“您教我‘手稳心狠’,我却学会了用针尖绣出春天。”
如今她的办公室里,还摆着那台母亲留下的蝴蝶牌缝纫机。
每年清明,她都会带着设计师去鄂西山区,在扶贫车间教留守妇女做苗绣改良时装。
有次直播带货,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改良旗袍,对着镜头展示袖口的盘扣:“这叫‘锦上添花’,就像咱们服装厂的姐妹们,总能在破茧处开出花来。”
林晚秋在汉派服装博物馆捐赠了三件展品:一件带着蝴蝶创可贴的旧工服,一本画满设计草图的《上海时装》,还有她母亲留下的樟木箱。
馆长问她有什么想说的,她指着箱子上的铜锁:“这里面锁着两代人的翅膀,现在终于能飞了。”
后来有人问起她成功的秘诀,林晚秋总会想起1995年那个暴雨夜。
当时她蹲在仓库门口,借着应急灯的光缝补被水泡坏的西装,针脚在布料上蜿蜒,像极了长江水在月光下的纹路。
“哪有什么秘诀,”她摩挲着食指上的茧,“不过是把每根线头都当成生命线来缝。”
及防。
林晚秋带着几个姑娘连夜打版,缝纫机的灯光映着她们年轻的脸。
当第一批绣着玉兰花的女裤摆上百货公司柜台,三天就卖断了货。
经理夫人再来时,手里的订单多了个零,她笑着说:“林厂长,该给你们厂换电动缝纫机了。”
12 重逢在展销会1991年秋,市工业品展销会开幕。
林晚秋穿着自己设计的米色风衣,站在“晚秋制衣”的展台前,身后是一排锃亮的电动缝纫机。
玻璃展柜里,最新款的女式套装领口别着玉兰花胸针,那是她特意让郊区的绣娘用真丝线绣的
髦衣裳,在林晚秋的针下都有了新的可能——就像她补在裤腰内侧的那朵迷你玉兰花,虽不显眼,却让整个衣裳有了贴着皮肉生长的妥帖。
9 服装厂的转机三个月后,街道办办起了集体服装厂,王主任第一个想到林晚秋:“你手艺好,来当技术骨干吧,带带那些小年轻。”
街道服装厂的日子像被熨斗烫过的布料,平整却带着灼痕。
林晚秋被分到后道组,专门处理成衣线头。
她的工位挨着窗户,能看见梧桐树上的麻雀把碎布头啄成窝。
组长何姐总说:“手要稳,心要狠,这活儿容不得半分心软。”
可林晚秋的指尖还是磨出了茧,她把创可贴剪成蝴蝶形状贴在指腹,夜里借着路灯绣鞋垫时,针脚依然细密如春雨。
转机出现在厂长女儿的婚宴。
厂里接了五百套西装订单,老师傅们为立体剪裁犯难。
林晚秋偷偷把自家陪嫁的樟木箱撬开,翻出母亲留下的《上海时装》老杂志。
她用废报纸画样版,在厕所隔间熬夜打版,最终做出的样衣让香港客商拍板:“就按这个版型来!”
11 改制风云10 改制风云1987年夏天,服装厂门口挂出“股份制改革”的横幅。
会计室算出的账目让人心惊:仓库积压了两万件滞销的蝙蝠衫,银行贷款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。
工人们在食堂吵翻了天,有人摔了搪瓷缸:“改制就是让我们下岗!”
林晚秋缩在角落,摩挲着新领的技师证,证书上的钢印还带着体温。
那晚她翻墙进厂,月光把裁剪台照得发白。
她铺开最新的巴黎时装周报道,在旧布料上画下收腰西装的草图。
第二天晨会,她把样衣往桌上一摊:“试试做职业女装吧,写字楼里的白领需要体面又耐穿的衣服。”
厂长盯着她熬红的眼睛,终于点头:“给你十个人,三个月内打开市场。”
12 下岗潮中的蝴蝶1988年秋,纺织业压锭的消息传来时,林晚秋的“梧桐巷”品牌已经打进武商百货。
她在车间办起夜校,教姐妹们用CAD设计软件,可当第一批下岗名单贴出来,还是有三十多个老姐妹抱头痛哭。
林晚秋把自己的股份分给她们:“跟我干,做汉派女装!”
她带着团队在汉正街租下门面,白天跑面料
。
“林厂长,有位先生找您。”
业务员的声音带着疑惑。
陈砚明站在战台边,军装上没有了肩章,脸色比从前苍白。
他手里攥着个布包,打开来是件洗得发白的衬衫,袖口还留着她当年补的针脚。
“小柔走了。”
他声音很低,“临终前说,当年车祸后她就该放手,不该拖累我们这么多年。”
林晚秋看着他鬓角的白发,突然想起那年在部队家属院,她蹲在地上给战士们补军装,陈砚明蹲下来帮她穿针,阳光从他肩章上跳下来,落在她手背上。
现在阳光依旧,只是针脚早已换了方向。
“这衬衫……”陈砚明摸着袖口的补丁,“你还能补吗?”
林晚秋接过衬衫,从展柜里拿出一盒新的的确良布料:“现在流行换袖口,我给您换个藏青色的边,再绣朵玉兰花吧。”
她抬头笑了笑,眼角的细纹里盛着经年的阳光,“不过得收加工费,两块钱。”
展销会的广播在大厅回荡,远处的缝纫机正在演示新款旗袍的剪裁。
陈砚明看着眼前的女人,她的风衣下摆被穿堂风吹起,像一只终于展开翅膀的蝴蝶。
他突然明白,有些情义不该是枷锁,而该是让对方飞翔的风。
“好。”
他说,“什么时候来取?”
林晚秋低头量着袖口尺寸,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:“等玉兰花再开的时候吧。”
她抬头望向窗外,展销会外的梧桐正落着黄叶,而远处的玉兰树,已经悄悄鼓起了新芽。
(全文完)
离婚后的人生开挂1 晨光里的裂痕1985年春,天还没透亮,林晚秋就摸黑起了床。
缝纫机在窗边投下沉默的剪影,她踩动踏板,给丈夫陈砚明的军装熨烫裤线,布料与熨斗接触时发出的“滋滋”声里,混着煤炉上熬小米粥的香气。
五斗橱上的座钟敲了七下,卧室门“咔嗒”打开。
陈砚明穿着白背心,发梢还沾着水珠,手里攥着听筒线——这通电话从凌晨四点响到现在,每隔半小时就来一次,都是医院打来的。
“晚秋,”他声音沙哑,“小柔的情况不太好,医生说需要专人陪护。”
林晚秋的手顿在裤腰处,熨斗在布料上烫出个歪斜的印子。
小柔是陈砚明的初恋,也是他当兵前定过亲的未婚妻,六年前一场车祸后瘫痪在床,未婚夫却成了她的丈夫。
这些年家里的药费单、护工费,她从未过问,直到昨夜陈砚明把离婚协议推到她面前。
“协议上写了,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你。”
他站在晨光里,肩章上的星徽冷冰冰的,“我欠小柔一条命,当年要不是为了救我……”粥锅突然咕嘟冒泡,米汤溢出来浇灭了煤火。
林晚秋转身关了火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她想起七年前嫁进陈家时,婆婆拉着她的手说:“砚明这孩子重情义,你跟着他,别怕受委屈。”
那时她以为,重情义是好事,直到现在才明白,有些人的情义像悬在头顶的刀,砍碎了别人的人生。
2 离婚日的缝纫机街道办的王主任推了推老花镜,看着眼前的离婚申请。
林晚秋盯着红本本上的烫金字,突然想起结婚那天,陈砚明用自行车载着她,军大衣裹住两人的腿,他说:“晚秋,以后我护着你。”
“考虑清楚了?”
王主任问,“你一个女人,没工作没孩子,离婚后怎么过?”
陈砚明的皮鞋在水泥地上碾出细响,他低头看表,袖口还沾着医院带回来的消毒水味。
林晚秋摸了摸帆布包里的东西——那是她陪嫁的蝴蝶牌缝纫机的说明书,边角都磨毛了。
嫁进来七年,她用这台缝纫机给陈家上下做了上百件衣裳,却从未给自己裁过一块新布。
“离吧。”
她听见自己的声音,像缝纫机断线时的轻响,“我签。”
走出街道办,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
陈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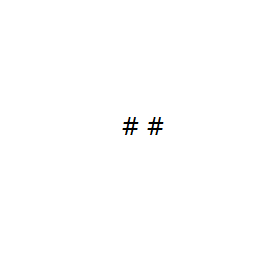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